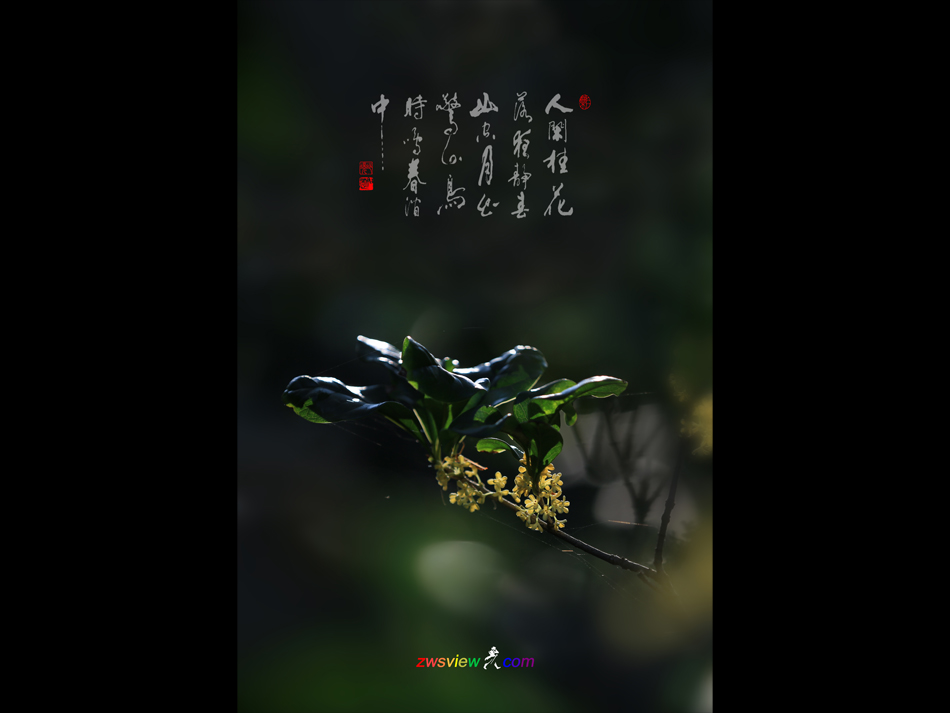《顽童》F0300000574 · 2015年10月18日摄于中国上海宝山
第一个结束的标志就是孩子懂得自主学习,理解学习的重要性,也更加愿意和父母交流自己的学习上的困难与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对于一些不好的事情上也能寻求父母的解决方案,更懂得和父母进行沟通和交流。第二个标志就是在生活中更加懂事,会常常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像是一些闲暇时间为父母做好下班的饭菜,或是为父母买生日礼物等等,一些生活中比较细心的小事,孩子都会记得很清楚,这样也会让父母觉得更加暖心。最后一个叛逆期结束的标志就是孩子会变得更加沉着稳定,更加清楚自己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无论生活还是学习上都会变得更加有条理,整体上各种事情上也会自己安排,让家长很少费心。

《油渣黄鱼片儿川》B0000000502 · 2023年5月28日摄于中国浙江杭州小河麵馆中河直街店
杭州的麺,干挑叫「拌川」,汤麺叫「片儿川」,在上海似乎不如本帮麺或苏式麺那样为人所熟知,但真的很好吃。
杭州麺其实很有些来头。胡乱猜测一下,应该在南宋时达到南北融合的鼎盛,若不然,《梦粱录》也不至于专门有一章节《麺食店》介绍南宋都城临安的麺食铺。文中列举的麺食,光名字看着就令人垂涎。
《梦粱录 · 麺食店》
南宋 吴自牧
向者汴京开南食麺店,川饭分茶,以备江南往来士夫,谓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以来,几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大凡麺食店,亦谓之「分茶店」。若曰分茶,则有四软羹、石髓羹、杂彩羹、软羊腰子、盐酒腰子、双脆、石肚羹、猪羊大骨、杂辣羹、诸色鱼羹、大小鸡羹、撺肉粉羹、三鲜大骨头羹、饭食。更有麺食名件:猪羊生麺、丝鸡麺、三鲜麺、鱼桐皮麺、盐煎麺、笋泼肉麺、炒鸡麺、大麺、子料浇虾麺、汁米子、诸色造羹、糊羹、三鲜棋子、虾棋子、虾鱼棋子、丝鸡棋子、七宝棋子、抹肉、银丝冷淘、笋燥齑淘、丝鸡淘、耍鱼麺。又有下饭,则有鸡、生熟烧、对烧、烧肉、煎小鸡、煎鹅事件、煎衬肝肠、肉煎鱼、炸梅鱼、鲑鲫杂焐、豉汁鸡、鸡、大鱼等下饭。更有专卖诸色羹汤、川饭,并诸煎肉鱼下饭。且言食店门首及仪式:其门首,以枋木及花样沓结缚如山棚,上挂半边猪羊,一带近里门面窗牖,皆朱绿五彩装饰,谓之「欢门」。每店各有厅院,东西廊庑,称呼坐次。客至坐定,则一过卖执箸遍问坐客。杭人侈甚,百端呼索取覆,或热,或冷,或温,或绝冷,精浇烧,呼客随意索唤。各卓或三样皆不同名,行菜得之。走迎厨局前,从头唱念,报与当局者,谓之「铛头」,又曰「着案」。讫行菜,行菜诣灶头托盘前去,从头散下,尽合诸客呼索,指挥不致错误。或有差错,坐客白之店主,必致叱骂罚工,甚至逐之。有店舍专卖苸麺,如大苸、大燥子、料浇虾、丝鸡、三鲜等苸,并卖馄饨。亦有专卖菜麺、熟齑笋肉淘麺,此不堪尊重,非君子待客之处也。又有专卖素食分茶,不误斋戒,如头羹、双峰、三峰、四峰、到底签,蒸果子、鳖蒸羊、大段果子、鱼油炸、鱼茧儿、三鲜、夺真鸡、元鱼、元羊蹄、梅鱼、两熟鱼、炸油河豚、大片腰子、鼎煮羊麸、乳水龙麸、笋辣羹、杂辣羹、白鱼辣羹饭。又下饭如五味麸、糟酱、烧麸、假炙鸭、干签杂鸠、假羊事件、假驴事件、假煎白肠、葱油炸、骨头米脯、大片羊、红大件肉、煎假乌鱼等下饭。素面如大片铺羊麺、三鲜麺、炒鳝麺、卷鱼麺、笋泼刀、笋辣麺、乳齑淘、笋齑淘、笋菜淘麺、七宝棋子、百花棋子等麺,皆精细乳麸,笋粉素食。又有专卖家常饭食,如撺肉羹、骨头羹、蹄子清羹、鱼辣羹、鸡羹、耍鱼辣羹、猪大骨清羹、杂合羹、南北羹、兼卖蝴蝶麺、煎肉、大麸虾等蝴蝶麺,及有煎肉、煎肝、冻鱼、冻鲞、冻肉、煎鸭子、煎鲚鱼、醋鲞等下饭。更有专卖血脏麺、齑肉菜麺、笋淘麺、素骨头麺、麸笋素羹饭。又有卖菜羹饭店,兼卖煎豆腐、煎鱼、煎鲞、烧菜、煎茄子,此等店肆乃下等人求食粗饱,往而市之矣。

《山芋》D0020000001 · 2016年7月27日摄于中国上海宝山
这只番薯在太小了,外婆没扔,塞在一次性塑料杯中,说看看能不能水培。几天之后,还真的发芽了,挺好看。
哈哈哈哈。
番薯,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名字:红薯、白薯、甘薯、红苕、地瓜等等等等。在上海,番薯被称为山芋。
番薯原产于南美,因高产、易种,被西班牙殖民者引入吕宋,即今菲律宾,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栽种。
公元16世纪末,福建人陈振龙下南洋时发现了番薯,觉得这种作物如果在老家栽种,应该能很好地解决当地乡亲的温饱。问题是,在当时的吕宋,殖民统治者西班牙人「珍其种,不与中国人」,违犯者会有牢狱之灾,甚至死刑。
通过细致观察,陈振龙发现,番薯可以通过其藤茎繁殖,而且,番薯的藤茎生命力极强,能耐较长时间的枯萎。于是,他私底下购得数截番薯藤,又找机会偷偷编入船上的缆绳中,抹上黄泥,最终成功地将这几截宝贵的薯藤带到了国内。那一年,是公元1593年。
回到家乡,陈振龙精心培育,第一年便大获成功。巧的是,那年福建恰逢大灾。陈振龙即向番薯栽培成功一事呈报给了福建巡抚金学曾。金学曾随即令陈振龙全面推广。数年之后,番薯作为重要的口粮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大面积种植,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人口也因此快速增长。
清道光年间,福州人在乌石山建造了「先薯祠」、「先薯亭」为纪念陈振龙和金学曾的无量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