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香肉丝饭》B0000000612 · 2024年5月22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吉野家国华广场店
吉野家推出新品:鱼香肉丝饭。今天特意去了离家最近的一家吉野家,位于国华广场的地下一层。
点了一个鱼香肉丝饭,一个麻婆豆腐,一个健康蔬菜。很本土。哈。
最近,吉野家一下子冒出了很多家新店。而在不久的过去,顶多也就两三年前,这家来自日本的大名鼎鼎的牛肉盖饭连锁在上海几乎销声匿迹。
很有点东山再起的架势。

《鱼香肉丝饭》B0000000612 · 2024年5月22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吉野家国华广场店
吉野家推出新品:鱼香肉丝饭。今天特意去了离家最近的一家吉野家,位于国华广场的地下一层。
点了一个鱼香肉丝饭,一个麻婆豆腐,一个健康蔬菜。很本土。哈。
最近,吉野家一下子冒出了很多家新店。而在不久的过去,顶多也就两三年前,这家来自日本的大名鼎鼎的牛肉盖饭连锁在上海几乎销声匿迹。
很有点东山再起的架势。

《小满手工粉》A0101040027 · 2024年1月30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悠方生活购物广场
街对面悠方生活购物广场地下一层的小满手工粉促销优惠:指定品种买一送一。两口子花了32元,算作一顿「520」烛光晚餐。哈。
今日小满。
元吴澄所撰《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
二十四节气中,小暑后有大暑,小寒后有大寒,小雪后有大雪,唯小满后无大满。小满是农时节气,也是处世之道:小富即安,小满即足。

《夏花》D0004000016 · 2024年5月16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新江湾城湿地
今天没去游泳。复旦大学江湾校区游泳馆今天有比赛,对外闭馆一天。
打恢复游泳以来,除了前一周六因故只游了100M被迫中断外,其他日子每天一个1000M,但体重没有明显减轻。
关于游泳能不能帮助减重,说法很多,且相互矛盾。有说可以,有说不可以。之前,我的经验是,游泳不能明显地减轻体重。我对这种现象的理解是,游泳能增肌减脂,减少的脂肪重量被增加的肌肉重量取代了,所以体重不减;另外就是,游泳可以增强代谢,同时也有促进吸收。
前几天,读到了一篇相关的科普文章,对游泳不减重的问题提出了作者的看法,觉得蛮靠谱的。
文章介绍说,游泳可以是有氧运动,也可以是无氧运动。这取决于游泳时的心律。如果维持较低心率,且时间较长,游泳是有氧运动,可以帮助减轻体重,反之则是无氧运动,无助于减重。心律控制的大致参考标准是:220减去年龄再乘以70%。也就是说,对于60岁的人而言,游泳时心律控制在112以下,就是有氧运动,可以帮助减重。时间越长,减重效果越明显。
另外一点也非常重要。游泳会增强饥饿感。如果游泳后增加进食,尤其是增加碳水化合物,不但不利于减重,很可能还会增重。

《金鸡独立》F0300000620 · 2024年5月18日摄于中国上海普陀
1月15日在儿童医院泸定路院区做了一次双膝外翻矫正手术,今天下午复诊。医生的结论是,恢复得很好。
下一次复诊被安排在七八月的暑期。

《花开富贵》D0021000001 · 2024年5月8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
我们家的绣球,开了。
绣球科绣球属木本植物。绣球原名「八仙花」,因花形酷似绣球,故得名。
绣球花很有意思,花的颜色依土壤的酸碱度而改变:土壤偏酸性为蓝色,偏碱性呈红色。而且,贯穿整个花期,花的颜色也会发生改变,很魔幻。
这株绣球别说开花,能活着都实属不易,甚至说是劫后余生也一点不为过。
去年,丫头买回家两珠盛花期的绣球。花谢之后,外婆没舍得扔,就放在阳台里,浇水、施肥,一直养着。今年早些时候,外婆发现其中一株的叶缘现枯萎貌,操起花剪彻彻底底地给修了一下。谁知到了开春,修剪过的那株再也没能萌出新芽来,反倒是被无视的这株,叶茂花繁,煞是兴旺。
真应了那句老话:「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哈哈。

《金鸡菊》D0004000015 · 2024年5月16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新江湾城湿地
金鸡菊,菊科金鸡菊属,一年或二年生草本,其中二年生草本金鸡菊的花期非常长,可从五月中旬一直持续到十月中旬,长达五个月。
金鸡菊有很多别名,如:小波斯菊、金钱菊、孔雀菊、大锦鸡菊等。
古人常以金钱菊为题作诗,如宋代的杨巽斋,曾作七绝一首,名即《金钱菊》:
清晓幽丛露作团,篱边积叠喜人看。
落英欲买真无价,唯许骚人罄一餐。
但此金钱菊彼金钱菊。金鸡菊原产美州,十九世纪才作为入侵物种传入中国,宋人不可能识。而宋人所识之金钱菊,很可能是旋覆花,菊科旋覆花属植物。因花形似金钱,故名金钱菊,为传统中药。

《南非万寿菊》D0004000017 · 2024年5月10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新江湾城公园
南非万寿菊,菊科植物,花色缤纷且花期很长,可从早春持续到盛夏。
之所以叫南非万寿菊,一是这种花原产南非,二是为和万寿花有所区别。万寿花原产中北美州,花形为球状,和南非万寿菊的花形有明显的不同,很好区分。

《招牌松鼠大桂鱼》B0000000611 · 2024年5月1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禧福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曾登门拜访过汪曾祺。那次,汪曾祺给孙郁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汪曾祺的家里「书不多,画倒不少。和他谈天,不怎么讲文学,倒是常常聊起民俗、戏曲、县志一类的东西。这在他的文章里也有体现。他同代的人写文章,都太端着架子,小说像小说,散文像散文,好像被贴了标签。汪曾祺不是这样。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杂家,深味文字之趣,精通杂学之道,境界就不同于凡人了。」
其实,只一篇《鳜鱼》,亦能大致领略出汪曾祺的杂来。
另:作为生于高邮的美食大家,在谈鳜鱼时竟然只字未提徽州的臭鳜鱼,多少有些令人遗憾。
《鳜鱼》
汪曾祺
读《徐文长佚草》,有一首《双鱼》:
如罽鳜鱼如鲋栉,鬐张腮呷跳纵横。
遗民携立岐阳上,要就官船脍具烹。
青藤道士画并题。鳜鱼不能屈曲,如僵蹶也。 音计,即今花毬,其鳞纹似之,故曰罽鱼。鲫鱼群附而行,故称鲋鱼。旧传败栉所化,或因其形似耳。
这是一首题画诗。使我发生兴趣的是诗后的附注。鳜鱼为什么叫作鳜鱼呢?是因为它「不能屈曲,如僵蹶也」。此说似有理。鳜鱼是不能屈曲的,因为它的脊骨很硬。但又觉得有些勉强,有点像王安石的《字说》。这种解释我没有听说过,很可能是徐文长自己琢磨出来的。但说它为什么又叫罽鱼,是有道理的。附注里的「即今花毬」,「毬」字肯定是刻错了或排错了的字,当作「毯」。「罽」是杂色的毛织品,是一种衣料。《汉书 · 高帝纪下》:「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这种毛料子大概到徐文长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所以他要注明「即今花毬」。其实罽有花,却不是毯子。用毯子做衣服,未免太厚重。用当时可见的花毯来比罽,原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且罽或 ,这个字十六世纪认得的人就不多了,所以徐文长注曰「音计」。鳜鱼有些地方叫作「鯚花鱼」,如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和我的家乡高邮。北京人则反过来读成「花鯚」。叫作「鯚花」是没有讲的。正字应写成「罽花」。鳜鱼身上有杂色斑点,大概古代的罽就是那样。不过如果有哪家饭馆里的菜单上写出「清蒸罽花鱼」,绝大部分顾客一定会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即使写成「鳜鱼」,有人怕也不认识,很可能念成「厥鱼」(今音)。我小时候有一位老师教我们张志和的「渔父」,「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就把「鳜鱼」读成「厥鱼」。因此,现在很多饭馆都写成「桂鱼」。其实这是都可以的吧,写成「鯚花鱼」、「桂鱼」,都无所谓,只要是那个东西。不过知道「罽花鱼」的由来,也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
鳜鱼是非常好吃的。鱼里头,最好吃的,我以为是鳜鱼。刀鱼刺多,鲥鱼一年里只有那么几天可以捕到。堪与鳜鱼匹敌的,大概只有南方的石斑,尤其是青斑,即「灰鼠石斑」。鳜鱼刺少,肉厚。蒜瓣肉。肉细,嫩,鲜。清蒸、干烧、糖醋、作松鼠鱼,皆妙。氽汤,汤白如牛乳,浓而不腻,远胜鸡汤鸭汤。我在淮安曾多次吃过「干炸鯚花鱼」。二尺多长的活治整鳜鱼入大锅滚油干炸,蘸椒盐,吃了令人咋舌。至今思之,只能如张岱所说:「酒足饭饱,惭愧惭愧!」
鳜鱼的缺点是不能放养,因为它是吃鱼的。「大鱼吃小鱼」,其实吃鱼的鱼并不多,据我所知,吃鱼的鱼,只有几种:鳜鱼、鮰鱼、黑鱼(鲨鱼、鲸鱼不算)。鮰鱼本名鮠。《本草纲目 · 鳞部四》:「北人呼鳠,南人呼鮰,并与鮰音相近,迩来通称鮰鱼,而鳠、鮠之名不彰矣。」黑鱼本名乌鳢。现在还有这么叫的。林斤澜《矮凳桥风情》里写了乌鳢,有人看了以为这是一种带神秘色彩的古怪东西,其实即黑鱼而已。
凡吃鱼的鱼,生命力都极顽强。我小时曾在河边看人治黑鱼,内脏都掏空了,此黑鱼仍能跃入水中游去。我在小学时垂钓,曾钓着一条大黑鱼,心里喜欢得怦怦跳,不料大黑鱼把我的钓线挣断,嘴边挂着鱼钩和挺长的一截线游走了!

《小巷》F0300000619 · 2024年5月13日摄于 中国上海青浦金泽古镇
五点起床,六点出门,七点抵达离家约75公里的金泽古镇。
江南水乡的格局都差不多,无非就是小桥流水、枕河人家。只是金泽的河网尤其的密,桥也就尤其的多。「出门即过桥,人家尽枕河」是对金泽最贴切的描述。
据说,金泽原有六观、一塔、十三坊、四十二虹桥。
桥,是金泽的最大看点。金泽人对桥似乎赋予了某种特殊的精神寄托。在金泽,「庙庙有桥,桥桥有庙」,这在其他地方并不多见。尽管现在很多依桥而立的寺庙早已不见了踪影,但在金泽人的心中,它们依然都还在的。我们用了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兜兜转转、寻寻觅觅,把万安桥、如意桥、普济桥、迎祥桥、放生桥、林老桥、天皇阁桥这七座现在的自宋至清的古桥逛了个遍,发现好几座古桥的桥堍依旧香火不断。

《巴厘岛爆满菠萝炒饭》B0000000609 · 2024年5月8日摄于中国上海青浦大虾泰泰蟠龙天地店
很多地方都有菠萝炒饭,尤其是东南亚,但通常认为,菠萝炒饭是泰国的一道经典美食。
菠萝炒饭的配料很多,像前几天在蟠龙天地「大虾泰泰」品尝的这个菠萝炒饭,能分辨出来的就有鸡蛋、鸡肉丁、虾仁、鱿鱼须、腰果、葡萄干、菠萝块等,口感和口味都相当丰富,酸、甜、香、鲜,非常可口。

《鲜肉小笼包》B0000000610 · 2024年4月30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苏小柳手工点心五角场分院
《汤包》
梁实秋
说起玉华台,这个馆子来头不小,是东堂子胡同杨家的厨子出来经营掌勺。他的手艺高强,名作很多,所做的汤包,是故都的独门绝活。
包子算得什么,何地无之?但是风味各有不同。上海沈大成、北万馨、五芳斋所供应的早点汤包,是令人难忘的一种。
包子小,小到只好一口一个,但是每个都包得俏式,小蒸茏里垫着松针(可惜松针时常是用得太久了一些),有卖相。名为汤包,实际上包子里面并没有多少汤汁,倒是外附一碗清汤,表面上浮着七条八条的蛋皮丝,有人把包子丢在汤里再吃,成为名副其实的汤包了。这种小汤包馅子固然不恶,妙处却在包子皮,半发半不发,薄厚适度,制作上颇有技巧,台北也有人仿制上海式的汤包,得其仿佛,已经很难得了。
天津包子也是远近驰名的,尤其是苟不理的字号十分响亮。其实不一定要到苟不理去,搭平津火车一到天津西站就有一群贩卖包子的高举笼屉到车窗前,伸胳膊就可以买几个包子。包子是扁扁的,里面确有比一般为多的汤汁,汤汁中有几块碎肉葱花。有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才出笼的,包子里的汤汁曾有烫了脊背的故事,因为包子咬破,汤汁外溢,流到手掌上,一举手乃顺着胳膊流到脊背。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不过天津包子确是汤汁多,吃的时候要小心,不烫到自己的脊背,至少可以溅到同桌食客的脸上。相传的一个笑话:两个不相识的人据一张桌子吃包子,其中一位一口咬下去,包子里的一股汤汁直飚过去,把对面客人喷了个满脸花。肇事的这一位并未觉察,低头猛吃。对面那一位很沉得住气,不动声色。堂倌在一旁看不下去,赶快拧了一个热手巾把送了过去,客徐曰:「不忙,他还有两个包子没吃完哩。」
玉华台的汤包才是真正的含着一汪子汤。一笼屉里放七八个包子,连笼屉上桌,热气腾腾,包子底下垫着一块蒸笼布,包子扁扁的塌在蒸笼布上。取食的时候要眼明手快,抓住包子的皱褶处猛然提起,包子皮骤然下坠,像是被婴儿吮瘪了的乳房一样,趁包子没有破裂赶快放进自已的碟中,轻轻咬破包子皮,把其中的汤汁吸饮下肚,然后再吃包子的空皮。没有经验的人,看着笼里的包子,又怕烫手,又怕弄破包子皮,犹犹豫豫,结果大概是皮破汤流,一塌糊涂。有时候堂倌代为抓取。
其实吃这种包子,其乐趣一大部分就在那一抓一吸之间。包子皮是烫面的,比烫面饺的面还要稍硬一点,否则包不住汤。那汤原是肉汁冻子,打进肉皮一起煮成的,所以才能凝结成为包子馅。汤里面可以看得见一些碎肉渣子。这样的汤味道不会太好。我不太懂,要喝汤为什么一定要灌在包子里然后再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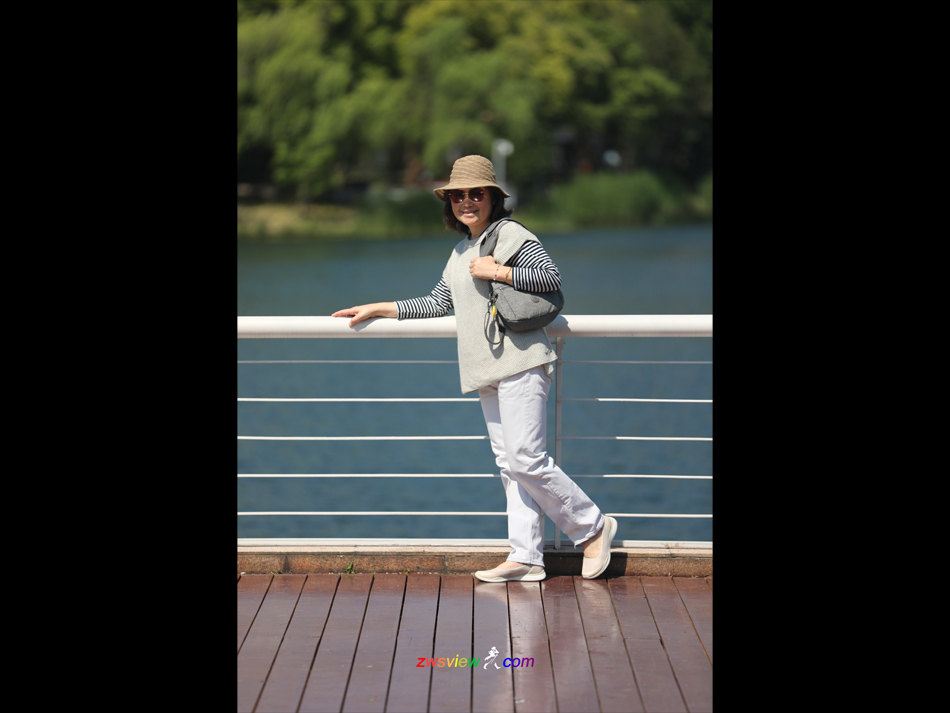
《新江湾城公园》F0300000618 · 2024年5月10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
新江湾城公园经过「拆围透绿」改造后重新开放。
最近这几年,上海似乎正在大力推进「拆围透绿」工作,已经拆除围墙的包括中山公园、复兴公园、鲁迅公园、世纪公园、和平公园以及一些机构等。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和上海音乐学院淮海路校区更是开启了建设开放式大学的先河。这些都给市民及游客提供了更多的休闲空间。
但,在「拆围透绿」上,上海显得很犹豫,比起很多其他城市不但起步晚,步伐也小。像重庆、四川、湖南、河南、黑龙江等地的很多城市,甚至把政府大院的围墙也都拆了。
上海加油!

《「拨霞供」》B0000000608 · 2019年8月30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
拨霞供,南宋时的一种涮锅。南宋美食家林洪在其所著食谱集《山家清供》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向游武夷六曲,访至止师,遇雪天,得一兔,无庖人可制。师云:『山间只用薄批,酒酱椒料沃之,以风炉安座上,用水少半铫。侯汤响一杯后 ,各分一筋,令自筴入汤、摆熟、啖之,及随宜各以汁供。』
林洪照方抓药,果然美味。吃到兴起,见了肉片都觉色如云霞。林洪不仅将此招吃法取名『拨霞供』,还赋诗一首:『浪涌晴江雪,风翻照晚霞』。」

《泰式古法咖喱大虾》B0000000607 · 2024年5月8日摄于中国上海青浦大虾泰泰蟠龙天地店
昨天难得朗晴,十点出门,开车30公里,跑去蟠龙天地转了转,散散心。中午,在一家叫「大虾泰泰」的泰国茶餐厅简单打了个尖。
两个人,点了两菜一饭:「泰式古法咖喱大虾」、「玛莎曼黄咖喱牛肉」和「巴厘岛爆满菠萝炒饭」。
菜名实在都太长了。如果是大酒店,那没什么问题。但对于主打快速、便捷的茶餐厅,感觉还是直接叫「咖喱大虾」、「咖喱牛肉」和「菠萝炒饭」更实用,也更接地气些。
菠萝炒饭最出彩,咖喱牛肉火候到位,但咖喱大虾稍嫌不足,主要是没怎么入味。
总体来说,这家店可以的。

《乳鸽》B0000000606 · 2024年4月29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匠心小厨悠方店
烤乳鸽,最初的源头是太平馆的红烧乳鸽,一道在二十五分钟之内完成卤汁、生炸、上桌的西菜。对的,这是一道西菜,而非粤菜,因为太平馆是一家中国人创办的西餐馆,创办人叫徐老高,之前曾在洋行帮厨,对西菜有一定的了解。
民国十二年,《民国日报》报道了一则新闻,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广州宴请高级将领享用太平馆的红烧乳鸽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孙中山说,他之所以来广州,是继续革命的未竟之业。第一步,「要使人人有饭喫」;第二步,「更要使人人都有好饭好菜吃」。但不能止步于此,「一定要更进一步,解救被残暴军阀欺凌压榨的全国同胞,让四万万同胞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饭菜,这么好的鸽子」。孙中山认为,「这才是革命最大的目的、最终的目标!」

《拆骨肉炖酸菜》B0000000605 · 2024年4月6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冰城老于家国和路店
几年前,雪村的一首洗脑神曲《东北人都是活雷峰》风靡大江南北,其中有一句歌词「翠花,上酸菜」无意间带火了东北人家餐桌上的当家花旦酸菜。
过去的东北,由于天寒地冻,每到冬季,当地既种不了叶菜,外面的叶菜也运不进来。为了在冬季能吃上叶菜,入冬前,家家户户都会贮存好几百斤大白菜,也就是所谓的「冬贮大白菜」。
大白菜的贮存通常有两种法子:窑藏和腌渍。后者,用东北人的话说,叫「渍酸菜」。这里的「渍」读作「积」。
关于如何渍酸菜,清朝文人徐宗亮在《黑龙江纪略》中有很详细的描述:「至秋末则惟黄芽白一种,土人以盐水浸之,储藏瓮中留冬春之需,谓之酸菜。」「黄芽白」指大白菜。上海人管大白菜叫「黄芽菜」。
渍酸菜,是一个发酵过程,期间会产生大量的乳酸菌。渍过的大白菜因此也就变成了酸菜。
在东北,酸菜有很多种吃法,可炖,可炒,可煮,也可以做成酸菜馅,比如酸菜炖白肉和酸菜饺子,极美味。

《焖罐牛肉》B0000000603 · 2023年12月3日摄于中国上海静安飞象西餐厅
焖罐牛肉,似乎是国内俄罗斯餐厅的菜单上必有的一道菜,据说屡次上过国宴。「焖罐」指的是一种烹饪方法,不光是牛肉,猪肉、羊肉、鸡肉、鱼,甚至像鹰嘴豆等素菜,都可以「焖罐」。
焖罐牛肉有点像江西的瓦罐汤,切成块的牛肉、土豆、胡萝卜、洋葱、番茄,或者还有西芹、蘑菇之类,外加高汤,可以先用大罐焖熟之后盛入小罐子保温,也可以直接用小罐子焖烤。比较有意思的是,用小罐子焖烤的话,罐子通常会用麺团封口。菜焖熟了,麺团也被烤成了麺包,蘸肉汤吃,很美味。

《辣肉麺》B0000000604 · 2024年4月5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浣纱制麵局
四千年前的中国人就已经在吃麺了。
二零零二年,考古工作者在喇家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保存完好的陶器,其中有一件篮纹红陶碗,略为倾斜地翻扣在地面上。当陶碗被提取后,人们发现陶碗下面的地面上残留有一堆碗状遗物,下层泥土,而和碗底接触的部位却呈现出清晰的麺条状结构。这些麺条状的物体粗细均匀,卷曲缠绕在一起,而且鲜有断头,其直径大约为0.3厘米,总长度不短于50厘米,呈纯正的米黄色。经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远研究员检测,认定陶碗中的遗物为麺条。后又经进一步成分分析,这些麺条的原料为大量的粟与少量的黍。除此之外,成分中还包括少量的油脂、类似藜科植物的植硅体以及少量动物的骨头碎片。
由此推断,这很可能是一碗四千多年前的「浇头麺」。

《挂画》C0000000084 · 2024年4月19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青年公社创智天地店
大约一周前,突然过敏,几乎可以确定是花粉过敏。
早就听说新冠可能导致过敏,没想到摊到自己头上了。如果不出意外,又是新冠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