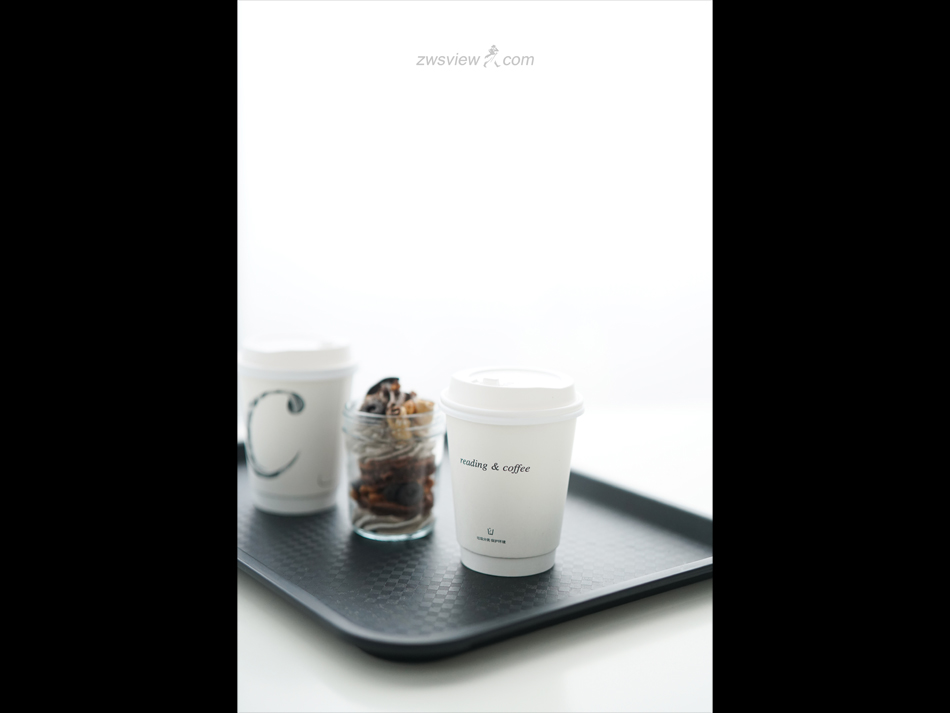《三林肉皮》B0000000493 · 2023年2月5日摄于中国上海浦东三林久久圆餐饮
有过一次因「密接」而被强制隔离一周的经历。
很幸运,在一家相当不错的商务酒店隔离,一日三餐也都出自正规餐饮公司。但吸烟是个问题。
在上海,所有公共场所,只要是室内,都在禁烟之列。隔离酒店肯定禁烟。这次,我很难得的独而不慎:带了两条烟和两个打火机进入酒店。理由是有的,在一个十几平米的狭窄空间,连续一周见不到任何人的情况下,维持情绪的稳定肯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为了尽可能少地给酒店添麻烦,我把所有容易吸味的物件,比如浴巾、洗脸巾、脚垫之类全部搬离卫生间,并将自己限制在淋浴房里吸烟。结束隔离,离开酒店前,将卫生间的四壁、顶和地面都用清洁剂仔细擦拭了一遍,尽可能彻底地去除烟味。前前后后搞了一个多小时,算是对自己做了坏事后寻求心理安慰必须的付出吧。哈哈哈哈。

《焼肉丼》B0000000481 · 2022年1月12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极火酱烧合生汇店
有一年独自去香港,从深圳的罗湖口岸过闸后,买了张地图,按图索骥地坐电车来到维多利亚港边上的星光大道。习惯性地掏出烟,叼了一支在嘴上,却没摸到打火机,于是抬头,想找人借火。令我诧异的是,路人都用诧异的眼了光看着我,仿佛我是外星人。
我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了。哪不对劲?我嘴里叼着烟?
环顾一众路人,确实没有一个在抽烟。
我把烟放回烟盒,找了个当地人,一问,果然,那一带属于禁烟区,即使是露天。抽烟需到指定的吸烟区。
庆幸自己反应快,避免了上千港元损失的同时,也诧异那些见我嘴里叼着烟的路人,竟然没有一个提醒一下。
从这次经历开始,但凡出境,都会事先了解一下当地的禁烟令。不想惹麻烦。

《青红椒虾酱啫啫五花肉》B0000000479 · 2023年6月16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几百度啫啫煲
每次出国,都会了解一下当地的入境政策,怕惹出不必要的麻烦。这个非常重要,比如电子烟,在一些国家被认定为违禁品,严禁携带入境。一旦查获,很可能会有牢狱之灾。对我来说,重点了解的是携带现金政策、食品的检疫政策,再就是可携带入境的香烟的数量。几乎很个国家对烟、酒的入关控制得非常严格,有的国家允许携带「合理数量」,有的只能携带不超过19支,即不可以携带整包的香烟,甚至,有的国家完全不允许携带烟草入境。
疫情前,去加拿大度假,计划待一个月。依我的吸烟量,起码要带六条香烟进关。而加拿大方面规定每人每次入境只能携带两条,即400支卷烟免税入境,多出部分必须申报并支付相应的关税。如此,我和外婆总共只有四条免税额。入境时,边境官问我有什么需要申报的,我如实回答说多带了两条烟,并询问可不可以加税后予以放行。边境官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声音说:「不要申报,不要吱声,这会儿海关官员们都在喝咖啡,不会注意你。赶紧进关,保证你不会有麻烦。」说完,还跟我做了一个鬼脸。
这算是一次有关香烟的有趣回忆。

《脆脆炸虾卷》B0000000477 · 2022年1月9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寿司福悠方店
对一个老烟枪来说,长途飞行是一个折磨。去日本,如果有选择,就先飞关西,然后搭乘新干线去关东。因为上海到关西的飞行时间比飞关东要短差不多一个小时。
长途飞行,经常需要转机。我会事先了解中转机场的吸烟室,这样到时候可以尽快地吸上烟。
印象中,有两次很要命。一次是飞北美,好像是多伦多,中途在达拉斯转机。事先上网查,说是中转机场可以吸烟。但那天,我硬是没找到吸烟室,这太让人抓狂了。那时美国签证还在有效期内,我甚至想先入境美国,找地方吸支烟再进机场转机。后来只是后程航班等待时间不多,这才作罢。另一次是在北海道新千岁机场。候机,准备回国。日本国内乘机是可以携带打火机的,所以一些机场便不再准备打火机。我是搭乘国内航司的航班,安检时不允许携带打火机进入机场。我以为在吸烟室里总可借到火,但最终未能如愿。那天进入吸烟室的人很少,仅碰到的两三个也都是吸的电子烟,无火可借。
回过头来想想,早年一边飞行一边吞云吐雾那是一种怎样的神仙日子啊。

《炸串》B0000000476 · 2023年7月2日摄于中国上海浦东大阪王将
这大半辈子,为了抽烟也是蛮拚的。
首先是穷。最开始,「飞马牌」就两毛八一盒,但买不起。幸好,很多烟纸店为做点小买卖都会把烟拆零了卖:一毛七支、七分五支、三分两支。现在回想起来,我抽得最多的,应该是三分两支这种。一是花钱不多,二是没有余烟需要藏。
有烟了,还得有地方抽。抽烟,要是被大人撞见,一顿揍是跑不了的。哪里安全?房顶。推开三层阁的老虎窗,很容易就上了房顶。只是那时房顶都是红瓦,很容易踩裂,导致漏雨,得找房管所来修。于是,不仅得躲大人,还得躲房管所,因为他们经常派人来「抓」。
大学时,有一年不知什么情况,卷烟特别难买。于是雪茄、烟斗,还有自己卷的「喇叭烟」,有什么抽什么。有一回外校同学来我们学校打比赛,我叼着雪茄去球场观赛。同学的带队老师一脸疑惑地问:「这是你同学还是老师?」

《秃黄油麺》B0000000471 · 2022年7月21日摄于中国上海黄浦裕兴记
戒烟七天,戒烟初期「三七二十一」三关之一。
「三」即头三天,体内尼古丁浓度急剧下降,最折磨人的一段时间。
「七」即七天,从这天开始,很多人会有一些症状出现,失眠、嗜睡、萎靡、失落、迷惘,甚至轻微抑郁。这些症状持续时间因人而异,据说个把月即可逐渐消失。
我猜测,这些症状很可能跟戒断尼古丁后减少了多巴胺的分泌不无关系。专家的建议是,戒烟时,尤其是像现在这样的阶段,可以增加一些运动,既可以转移注意力、打发时间,又可以增加多巴胺和内啡肽的分泌,缓解不适。
「二十一」即二十一天。通常认为,二十一天是一个新的生活习惯养成的时间。而戒烟就是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拭目以待。